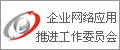南疆,大漠边缘。
车轮过后扬起的一卷灰尘,给路边残留的绿色再添一层灰黄的印记。古城、沙漠、地与天连成一片单调的昏黄,除了点点顽强的胡杨。
脚底,戈壁石垫造的小道,无边无际地笔直放肆延伸。极目,似乎看到了那高耸的粉罐,看下路标,距离还有11公里。烈日如往常一样,千百年来肆无忌惮地挥洒它势不可挡的光芒,一代一代地洗礼着头巾下依然干涸沧桑的维族老乡的脸。拂一拂额前的汗珠,继续前行。
干渴,蹲在路旁,打开背包,翻出大包资料下深埋的半瓶水。拧开,仰头,顺着水滴流下,喉咙深处甘甜清凉。“噔噔”声由远至近,一头黑色的毛驴低着头,在一声脆亮的鞭响后,死命地往前蹦跶两步。车上是一个维族老人,以及满车的草根。老人嘴里念叨着一串永远都听不懂的嘟噜声,紧缩双眉,满脸疑惑地看着路边蹲着的青年。驴车缓缓驶过,扬起的昏黄半晌后逐渐沉降。
继续前行,翻过一道土坡后,惊喜地发现居然有一条将近干涸的小河,白衬衫欢快跑下土坡,一头扎进水里,即使不那么清澈,不那么冰纯,但脸上洗去尘埃的那份爽快已无可言表。
带着眷恋,告别小河小草小羊,低头看一看口袋边缘醒目的LOGO,掂一掂包里客户急需的资料,继续前行。
高耸的粉罐越来越近,塔吊在这片戈壁深处毅然耸立,工地上两道红色的“彩虹”,依稀听到液压系统清晰的“嗖嗖”声,客户那熟悉的身影站在厂门口向这边翘首远望。拂去汗滴,欣然一笑,说道:“您好,我是三一重工的。”